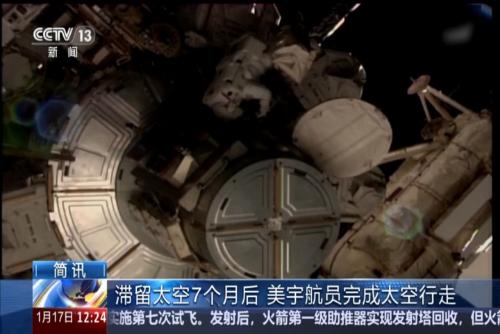东西问 | 瑞士汉学家胜雅律:我如何“观中国”?
中新社瑞士艾恩西德伦10月18日电 题:瑞士汉学家胜雅律:我如何“观中国”?
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

“律”和“智”,恐怕是瑞士知名汉学家胜雅律(Harro·von·Senger)学术生涯的两个“关键字”。
“律”指法律,是胜雅律的老本行;胜雅律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学院就读,后拿到法学博士学位,1982年起出任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顾问,对中国法律、中国法律制度史、中国法律思想史等颇为精通。
“智”指《智谋》,是胜雅律的成名作;1988年,胜雅律以德文写就详细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《智谋(上册)》(Strategeme, Band1),在西方学界引起极大震动,先后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;2000年至2001年,胜雅律出版《智谋(下册)》(Strategeme, Band2)、《计谋》(Die List)、《智谋书》(Die Kunst der List)等著作,2008年又出版了一部专门介绍谋略的著作。
胜雅律是公认的“中国通”。读大学时胜雅律开始学习汉语,1970年发表的法学博士论文以传统中国买卖合同为主题,这是第一篇由瑞士人所写有关中国法律的法学博士论文;1975年至1977年,胜雅律以瑞士公派留学生身份在北京大学就读,待1978年中国打开“国门”,几乎每年访问中国,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,发表了大量以中国法律、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。
身为法学家、汉学家和“中国通”,如何观察和理解中国?近日,胜雅律在其定居的瑞士北部小镇艾恩西德伦接受了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记者:您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三十六计,出版了多部著作,认为“无论东西方,三十六计表现的是普遍的行为模式”;在您看来,这其中凝聚了怎样的智慧?
胜雅律:我想用太极图回答这个问题。可以说,太极图黑色的一半代表“奇”,白色的一半代表“正”,两部分组成一个统一体。在人生中用“正”即白色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,同样用全“奇”即黑色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的,需要把“正”和“奇”结合起来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看看用“正”还是用“奇”的方法好。
同时,不能因为太极图中黑白各占一半就认为“正”所发挥的作用和“奇”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大,我认为要“以正为主,以奇为辅”,重要的是尽量用“正”的方法解决问题。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解决问题,实在不行再在法律和伦理允许范围内用“奇”的方法。从我的经验看,大部分问题都可以用“正”的方法解决,少数问题才需要用“奇”的方法。中国三十六计凝聚了“奇”的智慧,给人们提供了在“奇”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,让人们能够比较容易“因地制宜”地找到一个具体方法来“出奇制胜”。
有些人对三十六计或者说对计谋持负面看法,但我认为,不应该轻视小的东西,小的东西有时候影响巨大。比如新冠病毒那么小,人的肉眼都看不见,却对世界影响这么大。因此“雕虫小技”一类的说法比较肤浅。
中新社记者:为什么您的研究后来从三十六计上升到了谋略?您如何理解谋略?
胜雅律: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智慧不限于“奇”,还包括“正”,这种兼顾“奇”和“正”处理问题的智慧,我称之为谋略。谋略包括“正”的思想,比如“治国之道必先富民”,也包括“奇”的思想,比如“藏巧守拙韬光养晦”,它的范围很广,因此要想全盘了解中国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,就要研究谋略,只研究计策是不够的。
谋略代表着长期规划和布局。1985年,我在中国报纸上读到中国领导人的一篇报告,讲到21世纪中叶,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后,要把中国建成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强国,我当时很震惊,后来在瑞士重要的《新苏黎世报》发表文章,专门把“2049年”放到文章副标题,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“百年目标”——它的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了西方各种战略规划,这也是谋略的一方面。

中新社记者:2017年您出版的《瑞士之道》,为什么用中国《道德经》里的智慧描述瑞士的治国之策?
胜雅律:1971年到1973年,我在台湾留学,第一次接触到老子的《道德经》,当时觉得非常陌生,里面的思想好像“没有英雄气质”,没有“强大和斗争”,似乎同西方人没有多大关系,是典型的“中国人思维方式”,但后来我重读《道德经》,想法开始转变。
上世纪90年代,我突然觉得《道德经》恰好是瑞士这个国家处世的蓝本,所以用几乎100条《道德经》“语录”解释瑞士的处世方式,比如“小国寡民”“无为”“不争”等思想,与瑞士的小国身份、中立原则等非常符合。可以说约2500年前,已有一位中国智者阐明了今天的瑞士的处世艺术。《瑞士之道》出版后,《新苏黎世报》写了书评,不过用中国哲学思想来解释瑞士,还需要时间让人接受。
中新社记者:为什么您说自己是西方少有的重视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?哪一点让您印象深刻?
胜雅律:1975年到1977年,我在北京大学留学,期间学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,希望了解它对中国现实的影响。之后我慢慢认识到,我在瑞士所学的法学(备注:留学前胜雅律已拿到苏黎世大学法学博士学位)和在北京大学所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,法学关心规范世界,马克思主义关心改造世界,可以说都属于“干预性”(Interventional)思想体系。
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,我印象最深的是主要矛盾理论及其政治实践。我认为,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来确立政治路线,主要矛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发挥具体影响的关键部分,比如过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”,现在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”,主要矛盾发生转化,各项具体方针和政策都相应发生了变化。

中新社记者:您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时候,非常重视中国官方文件和法律法规,强调要把现象学方法和规范学方法相结合,为什么?
胜雅律:我是苏黎世大学的法学博士,也是一名瑞士律师,学术生涯伊始就很重视法律法规和官方文件,也习惯于阅读和分析规范性材料以及不那么“诗情画意”、在很多人看来“枯燥无聊”的表达方式。我用规范学方法研究中国官方文件,是为了预见未来中国的发展,因为通过这些文件可以研究中国对未来的设想、未来方向以及目标。
接下来,当然还要看现实情况,这就变成现象学考察,即通过考察各种实在的现象来了解那些设想的实践情况;根据我的经验,中国各领域基本都在按官方文件的设想发展。
中新社记者:对于西方业界,您强调在观察和研究中国时要“设身处地”和“感同身受”,摒弃意识形态和偏见的干扰,否则就会误判中国形势,您能否详细阐述?
胜雅律:我认为西方业界最根本的问题是不重视认识论。西方政治家、新闻记者或者智囊,都认为认识世界非常简单,只要睁开眼睛,看看统计,现场考察,采访一些人,最后把搜集的材料用西方各种各样的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心理、历史等理论和经验加以分析,就可以得出“正确的认识”。其实,认识世界不是那么简单。
比如阿富汗战争,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打了近20年的仗,结果全盘失败,他们战败不是因为武器不好、不愿花钱、害怕牺牲等等,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不了解阿富汗的国情,看不到认识论的重要性。
又比如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和报道中国,陷入“西方自我中心”的死角,也是因为认识论出现问题,潜意识里把西方视作“当代文明的创造者”,将西方的科技优势代入人文领域,认为西方是民主、人权的“老师”,觉得自己非常“高明”,由此滋生傲慢和偏见,无视或者不愿承认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变化。
这里我想介绍我提倡的认识论——“全顾学方法论”,它要求在分析、解决问题时必须“全顾一切方面”,从多种意识形态出发加以学习研究,因为不同意识形态对“问题一切方面”的看法并不一样,这意味着从多个意识形态看问题要优于从单一意识形态看问题。
因此我很高兴在北京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,它拓展了我认识世界的视野,完全符合“全顾学方法论”的要求;另一方面,依靠这一方法,我在研究中国法律之余,兼顾了中国文化的其它方面,“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”,研究中国三十六计就是我“兼收并蓄”的收获之一。(完)
受访者简介:

胜雅律,瑞士知名汉学家,德国弗赖堡大学汉学专业终身教授,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顾问;1988年出版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专著《智谋(上册)》,其后出版《智谋(下册)》《谋略》等著作,2011年翻译出版德文版《孙子兵法》,2017年出版《瑞士之道》,2020年出版《给法律人士的36计》,2021年出版《中国民法典中的继承法》;精通中国法律、中国法律制度史、中国法律思想史等,多年来发表了大量以中国法律、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。
相关新闻:
国内新闻精选:
- 2025年01月20日 21:31:18
- 2025年01月20日 17:54:16
- 2025年01月20日 14:37:30
- 2025年01月19日 23:21:36
- 2025年01月19日 18:21:53

 参与互动
参与互动